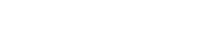人在大宋:忽悠慕容复替我打工 作者:佚名
第十章 舅甥相见,话离別,初论武
……
一个手持汤药侍立在旁,另一个剪了灯花又去照看铜盆里的炭火,显然都不是正主。
赵令甫把视线移向床榻,借著床头豆油灯那不算亮堂的光线,分明看见一个形容枯槁的年轻人。
是的,年轻人!
二十出头的年纪,面容瘦削,两腮和眼窝都是陷进去的,还泛著病態的青黑。
许是刚喝了药,嘴唇倒是不干,但仍旧没什么血色。
“是三郎么!”
听见脚步声进来,年轻人激动地扯著喉咙,嗓音沙哑地问了一声,同时又挣扎著想从床上坐起来,惊得身边僕人连忙去搀扶。
这声呼唤里,满含著割捨不断的血脉亲情,即使如今的赵令甫听了,也不免动容。
快走几步,近到榻前,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泪湿眼眶,口呼:“舅父!”
非是他惺惺作態,这一跪,一是因为顶替了赵令甫的身份,二是因为一路走来实在艰辛,直到现在见了这位舅父,才终於有几分归属感。
娘亲舅大!
光这一句,就能看出舅舅的地位!
王晟情绪波动很大,止不住地咳嗽,胸口剧烈起伏,侍者忙给他拍背顺气,好一阵才平缓过来。
颤巍巍伸出一只瘦到能显出青筋的手来,断续说道:“来!咳咳!上前来!”
双亲走得早,“长姐如母”四个字对王晟来说再合適不过。
在他七岁时,长姐嫁给了宗室子赵世居,不想这一別就是十七载!
虽然这些年里,姐弟俩也有过书信往来,但毕竟相隔千里,到底不那么便宜。
今夏得知姐夫涉嫌谋逆大罪时,他可是好一番著急上火,嘴上都急出了一圈燎泡。
想托关係找人情,可他连官场都不曾入,又哪有那个门路?
后来听说姐夫已经被赐死,姐姐与几个外甥则被圈禁关押,他也就不做別的指望了。
毕竟不管怎么说,起码人还活著!
可谁想到,今夜竟突然有人找上门,报信说有流民暴乱,目標直指他王家。
再一问,来人竟是护送他那小外甥从汴京一路寻来的!
这让他惊慌、疲惫之余,又多了几分期待与惊喜,才一直强撑著不肯睡去,非要见一见本人不可。
赵令甫膝行两步,从怀里掏出母亲给的那封亲笔信,双手递了上去,又唤了一声:“舅父!”
王晟接过信,单见信封上那一笔端庄柔润的楷书,便能確信是长姐亲笔无疑!
不著急看信中內容,只看向眼前这个五岁大的孩童,眉眼间果然多有长姐的温和,皮肤白净。
“好孩子!快起来!”
说话间,他还试图用手去拉赵令甫起身,只是臂膀上属实没多少力气。
赵令甫哪忍心叫舅父吃力,稍一感受,便趁势站起。
他个头不高,床榻也不矮,王晟半坐在床上,舅甥二人说话倒正方便。
不过还没说上几句,王晟又剧烈咳嗽起来,好似要將肺管子都咳出来一般!
旁边的侍者被唬得不轻,一边帮他顺气,一边试著劝道:“大官人,小郎君连日赶路实在辛苦,眼下时候也晚了,不如且先沐浴歇下,往后有日子聊呢!”
王晟这时候才发觉自家外甥面上的疲惫,紧握著他的小手,又用力拍了两下,方才止住咳嗽说道:“也好!也好!且带三郎去歇下,务必好生照料!”
“是!”,侍者恭敬应下,隨后又面向赵令甫道,“小郎君,请隨我来!”
赵令甫闻言,也没再多待,只行礼別了舅父,便跟著侍者从房中退出来。
这一夜兵荒马乱,当真把人折腾的够呛,要是再不歇下,天可就真亮了。
没有更多讲究,几个僕从直接將眾人带去厢房,安排得很妥当。
赵令甫今日实在是累坏了,幼稚的身体根本经不起这般折腾,方一躺下便沉沉入梦。
一觉醒来,已过了午时,日头正盛。
在两个船场僕妇的照料下,赵令甫梳洗一番之后,得知舅父还在歇息,便去寻了忠伯、杨叔和沈先生。
“三位叔伯在聊什么?”
他今日的心情不错,毕竟昨夜舅父对他的態度,可是远远超出了预期。
杨怀义有些不好开口,还是沈先生替他言道:“杨都头有意返回汴京,正在考虑何日启程。”
赵令甫闻言愕然,诧异道:“杨叔要走?”
杨怀义点了点头,道:“是啊!我此行就是为了把三郎安稳送到苏州,如今既然三郎已到了舅家,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,也是时候回京,重返疆场!”
他到底与李忠、沈樵等人不同,他是军伍世家出身,心中还有一番沙场建功、戍边卫国的抱负,总不好就这么一直糊里糊涂地留在苏州过安稳日子。
赵令甫听完这话便也明白过来,有些事终究不能强求,於是沉默良久,方才问道:“杨叔打算何日归京?”
杨怀义也在为难:“还未想好,毕竟来这一趟,还未当面拜会过主家,就此离去实在失礼!”
赵令甫微微点头,又展顏笑道:“若杨叔不急,不如且再多留几日,或许过两天魏叔便带著安神医来了,杨叔难道不想与安神医见上一面吗?”
杨怀义闻言也觉有理,便点头应下:“也好!那就依三郎的,再留几日!”
赵令甫又看向忠伯和沈先生,苦笑道:“忠伯和先生不会也要弃我而去吧?”
这话一出,二者当即表態:“少公子说的这叫什么话?我等受主公大恩,自然是要留下听候少公子差遣的!只盼少公子將来不要嫌弃我等本领低微就好!”
此言多有顽笑成分,杨怀义听了却觉有几分不自在,也补了一句:“某家要走,並非是弃三郎而去,只是吴地安寧,无我这般军卒用武之地。”
“若三郎日后有事需我出力,只消一封书信,即便相隔千里万里,某家也绝不会推諉迟疑!”
以杨怀义的性格,说出这话,赵令甫还是信的。
“杨叔不必如此,我省得的!只是可惜,本来还想著等此番安顿下来,能请杨叔教我些武艺,现在看来,却是我没这个福气了。”
这话说的颇有些遗憾,也確实是他心中真实想法。
杨怀义却很意外:“三郎竟想习武?”
不怪他诧异,本朝重文轻武的风气是自太宗皇帝起便有的,此后歷代官家也都秉持著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理念,所以武人地位一直都很低下。
赵令甫自然没这种偏见,理所应当道:“习武能保家卫国、开疆拓土,还能行侠仗义、强身健体,有何不好?”
杨怀义一听此言,心中更是如同饮了杯美酒般畅快!
果然不愧是太祖皇帝的血脉,也不愧是世居兄的血脉!
“那三郎是想学什么样的功夫?”,他此时也来了兴致,不禁问道。
这可把赵令甫给问住了,疑惑道:“什么样的功夫?”
难道是指哪个门派的功夫?
杨怀义给他解释道:“这杀人的功夫和打人的功夫不一样,沙场征战的功夫和走脚押鏢的功夫又不一样,所以想学功夫,你就先得明白自己为什么习武!”
……
第十章 舅甥相见,话离別,初论武
……
一个手持汤药侍立在旁,另一个剪了灯花又去照看铜盆里的炭火,显然都不是正主。
赵令甫把视线移向床榻,借著床头豆油灯那不算亮堂的光线,分明看见一个形容枯槁的年轻人。
是的,年轻人!
二十出头的年纪,面容瘦削,两腮和眼窝都是陷进去的,还泛著病態的青黑。
许是刚喝了药,嘴唇倒是不干,但仍旧没什么血色。
“是三郎么!”
听见脚步声进来,年轻人激动地扯著喉咙,嗓音沙哑地问了一声,同时又挣扎著想从床上坐起来,惊得身边僕人连忙去搀扶。
这声呼唤里,满含著割捨不断的血脉亲情,即使如今的赵令甫听了,也不免动容。
快走几步,近到榻前,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泪湿眼眶,口呼:“舅父!”
非是他惺惺作態,这一跪,一是因为顶替了赵令甫的身份,二是因为一路走来实在艰辛,直到现在见了这位舅父,才终於有几分归属感。
娘亲舅大!
光这一句,就能看出舅舅的地位!
王晟情绪波动很大,止不住地咳嗽,胸口剧烈起伏,侍者忙给他拍背顺气,好一阵才平缓过来。
颤巍巍伸出一只瘦到能显出青筋的手来,断续说道:“来!咳咳!上前来!”
双亲走得早,“长姐如母”四个字对王晟来说再合適不过。
在他七岁时,长姐嫁给了宗室子赵世居,不想这一別就是十七载!
虽然这些年里,姐弟俩也有过书信往来,但毕竟相隔千里,到底不那么便宜。
今夏得知姐夫涉嫌谋逆大罪时,他可是好一番著急上火,嘴上都急出了一圈燎泡。
想托关係找人情,可他连官场都不曾入,又哪有那个门路?
后来听说姐夫已经被赐死,姐姐与几个外甥则被圈禁关押,他也就不做別的指望了。
毕竟不管怎么说,起码人还活著!
可谁想到,今夜竟突然有人找上门,报信说有流民暴乱,目標直指他王家。
再一问,来人竟是护送他那小外甥从汴京一路寻来的!
这让他惊慌、疲惫之余,又多了几分期待与惊喜,才一直强撑著不肯睡去,非要见一见本人不可。
赵令甫膝行两步,从怀里掏出母亲给的那封亲笔信,双手递了上去,又唤了一声:“舅父!”
王晟接过信,单见信封上那一笔端庄柔润的楷书,便能確信是长姐亲笔无疑!
不著急看信中內容,只看向眼前这个五岁大的孩童,眉眼间果然多有长姐的温和,皮肤白净。
“好孩子!快起来!”
说话间,他还试图用手去拉赵令甫起身,只是臂膀上属实没多少力气。
赵令甫哪忍心叫舅父吃力,稍一感受,便趁势站起。
他个头不高,床榻也不矮,王晟半坐在床上,舅甥二人说话倒正方便。
不过还没说上几句,王晟又剧烈咳嗽起来,好似要將肺管子都咳出来一般!
旁边的侍者被唬得不轻,一边帮他顺气,一边试著劝道:“大官人,小郎君连日赶路实在辛苦,眼下时候也晚了,不如且先沐浴歇下,往后有日子聊呢!”
王晟这时候才发觉自家外甥面上的疲惫,紧握著他的小手,又用力拍了两下,方才止住咳嗽说道:“也好!也好!且带三郎去歇下,务必好生照料!”
“是!”,侍者恭敬应下,隨后又面向赵令甫道,“小郎君,请隨我来!”
赵令甫闻言,也没再多待,只行礼別了舅父,便跟著侍者从房中退出来。
这一夜兵荒马乱,当真把人折腾的够呛,要是再不歇下,天可就真亮了。
没有更多讲究,几个僕从直接將眾人带去厢房,安排得很妥当。
赵令甫今日实在是累坏了,幼稚的身体根本经不起这般折腾,方一躺下便沉沉入梦。
一觉醒来,已过了午时,日头正盛。
在两个船场僕妇的照料下,赵令甫梳洗一番之后,得知舅父还在歇息,便去寻了忠伯、杨叔和沈先生。
“三位叔伯在聊什么?”
他今日的心情不错,毕竟昨夜舅父对他的態度,可是远远超出了预期。
杨怀义有些不好开口,还是沈先生替他言道:“杨都头有意返回汴京,正在考虑何日启程。”
赵令甫闻言愕然,诧异道:“杨叔要走?”
杨怀义点了点头,道:“是啊!我此行就是为了把三郎安稳送到苏州,如今既然三郎已到了舅家,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,也是时候回京,重返疆场!”
他到底与李忠、沈樵等人不同,他是军伍世家出身,心中还有一番沙场建功、戍边卫国的抱负,总不好就这么一直糊里糊涂地留在苏州过安稳日子。
赵令甫听完这话便也明白过来,有些事终究不能强求,於是沉默良久,方才问道:“杨叔打算何日归京?”
杨怀义也在为难:“还未想好,毕竟来这一趟,还未当面拜会过主家,就此离去实在失礼!”
赵令甫微微点头,又展顏笑道:“若杨叔不急,不如且再多留几日,或许过两天魏叔便带著安神医来了,杨叔难道不想与安神医见上一面吗?”
杨怀义闻言也觉有理,便点头应下:“也好!那就依三郎的,再留几日!”
赵令甫又看向忠伯和沈先生,苦笑道:“忠伯和先生不会也要弃我而去吧?”
这话一出,二者当即表態:“少公子说的这叫什么话?我等受主公大恩,自然是要留下听候少公子差遣的!只盼少公子將来不要嫌弃我等本领低微就好!”
此言多有顽笑成分,杨怀义听了却觉有几分不自在,也补了一句:“某家要走,並非是弃三郎而去,只是吴地安寧,无我这般军卒用武之地。”
“若三郎日后有事需我出力,只消一封书信,即便相隔千里万里,某家也绝不会推諉迟疑!”
以杨怀义的性格,说出这话,赵令甫还是信的。
“杨叔不必如此,我省得的!只是可惜,本来还想著等此番安顿下来,能请杨叔教我些武艺,现在看来,却是我没这个福气了。”
这话说的颇有些遗憾,也確实是他心中真实想法。
杨怀义却很意外:“三郎竟想习武?”
不怪他诧异,本朝重文轻武的风气是自太宗皇帝起便有的,此后歷代官家也都秉持著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理念,所以武人地位一直都很低下。
赵令甫自然没这种偏见,理所应当道:“习武能保家卫国、开疆拓土,还能行侠仗义、强身健体,有何不好?”
杨怀义一听此言,心中更是如同饮了杯美酒般畅快!
果然不愧是太祖皇帝的血脉,也不愧是世居兄的血脉!
“那三郎是想学什么样的功夫?”,他此时也来了兴致,不禁问道。
这可把赵令甫给问住了,疑惑道:“什么样的功夫?”
难道是指哪个门派的功夫?
杨怀义给他解释道:“这杀人的功夫和打人的功夫不一样,沙场征战的功夫和走脚押鏢的功夫又不一样,所以想学功夫,你就先得明白自己为什么习武!”
……